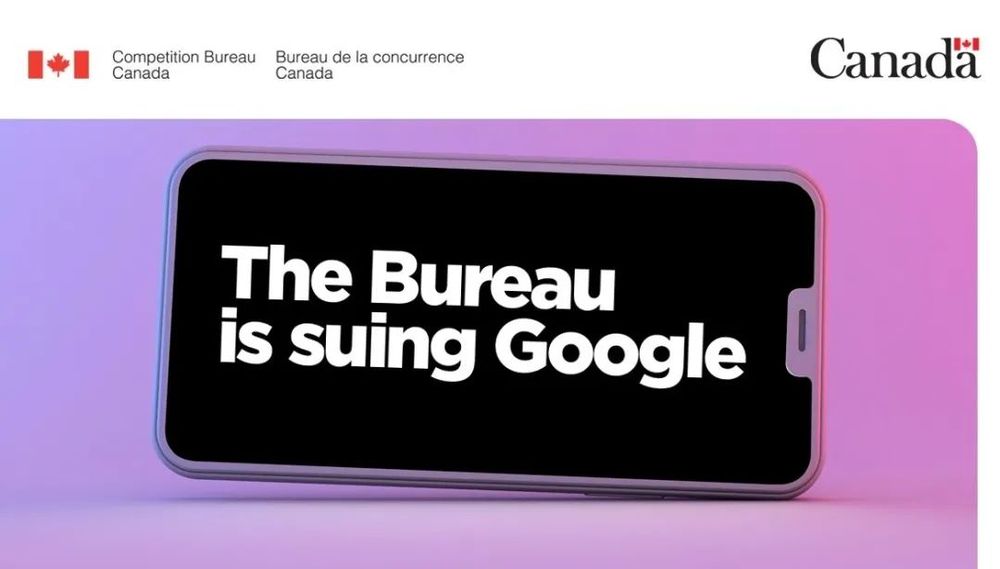有谷歌框架可以翻墙吗
我感到非常幸运能够亲历了谷歌上市后的早期时期。与大多数公司不同,与流行的叙事相反,谷歌的员工,从初级工程师一直到高管,都是真正关心做正确事情的好人。
当时那经常被嘲笑的“不作恶”确实是公司的指导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像微软这样的同时代公司的反应,这些公司的运营程序将利润远远置于客户和整个人类利益之上)。
许多时候,我看到谷歌因其真诚地试图造福社会而受到批评,比如谷歌图书项目。围绕Chrome和Search,尤其是在广告方面被指责存在冲突利益的批评往往是站不住脚的(令人惊讶的是巧合和错误在表面上经常被误解为恶意)。我经常看到隐私倡导者以对用户净有害的方式反对谷歌的提案。
其中一些争议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最让人讨厌的之一就是我们今天不得不穿越的无谓的cookie警告的普及。我发现团队通常在积极追求对世界有益的想法,而不是将短期的谷歌利益置于首位,却常常在公众舆论的法庭上遭到怀疑,这让我感到相当沮丧。
早期的谷歌也是一个出色的工作场所。高管每周都坦率回答问题,或者坦白地解释无法这样做的原因(比如法律原因或某些话题过于敏感)。埃里克·施密特定期向整个公司介绍董事会的讨论。对各种产品的成功和失败进行了相对客观的呈现,成功被庆祝,而失败则被批判性地审查,目的是吸取教训而不是归咎。公司有一个愿景,对该愿景的偏离会进行解释。与我在Netscape实习时经历的迪尔伯特级别的管理相比,谷歌员工的整体能力让人耳目一新。
在谷歌的前九年里,我的工作重点是HTML和相关标准。我的任务是为网络做最好的事情,因为对网络有利的任何事情都对谷歌有利(我明确被告知忽略谷歌的利益)。这是我在Opera Software工作时开始的工作的延续。谷歌是这一努力的出色东道主。
我的团队名义上是谷歌的开源团队,但我完全是独立的(这要感谢克里斯·迪博纳)。我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谷歌校园的不同建筑中使用笔记本电脑完成的;整整几年过去了,我几乎没有使用过我的指定办公桌。
随着时间的推移,谷歌文化的例外情况逐渐出现。例如,尽管我喜欢维克·贡多特拉的热情(以及他对谷歌+的最初愿景,这个愿景相当明确,虽然不一定被一致赞赏,但至少是明确的),但我对他在事情发展不如预期时能否给出明确答案的能力感到不太自信。他还开始在谷歌引入了一些隔离措施,这与早期谷歌的完全内部透明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另一个例子是Android团队(最初是一项收购),他们从未真正完全适应谷歌的文化。Android的工作/生活平衡不健康,团队的透明度不如谷歌早期的部分,并且团队更注重追逐竞争对手,而不是解决用户的实际问题。
我在谷歌的最后九年花在了Flutter上。我在谷歌的这段时间里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就是这个努力的早期阶段有谷歌框架可以翻墙吗。Flutter是谷歌旧体系中最后推出的项目之一,是在成立Alphabet之前由拉里·佩奇启动的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实验之一。我们基本上像一家初创公司一样运作,更多地是在发现我们在构建什么,而不是在设计它。
Flutter团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年轻的谷歌文化构建的;例如,我们重视内部透明度、工作/生活平衡和数据驱动的决策。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开放,这使得我们很容易在这一努力周围构建一个健康的开源项目。Flutter在所有这些年里也非常幸运,拥有出色的领导团队,比如创始技术负责人亚当·巴思,PM蒂姆·斯尼斯和工程经理托德·沃尔克特。
在最初的几年里,我们没有遵循工程最佳实践,例如没有编写测试,文档也很少。核心 Widget、RenderObject 和 dart:ui 层的设计文档就是这块白板。这让我们一开始能够快速推进,但后来我们为此付出了代价。
Flutter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迅速发展,与谷歌同时经历的变化相对独立。谷歌的文化逐渐瓦解,决策从为用户利益而做出的,转变为为谷歌利益而做出的,最终变为为做出决策的人的利益。透明度消失了。
曾经我会热切参加每一次公司范围的会议以了解发生了什么,但现在我发现自己能够逐字逐句地预测高管们会给出的答案。如今,在谷歌我找不到任何人能够解释谷歌的愿景。士气达到了历史最低点。如果你与旧金山湾区的心理医生交谈,他们会告诉你他们的谷歌客户对谷歌感到不满。
然后,谷歌进行了裁员。裁员是一次无谋的错误,是由于短视的追求确保股价季度内持续增长,而不是按照谷歌先前的战略,即优先考虑长期成功,即使这会导致短期亏损(即“不作恶”的本质)。裁员的影响是潜在的。在此之前,人们可能会关注用户,或者至少关注公司,相信做正确的事情最终会得到回报,即使这并不严格属于他们分配的职责范围。
但在裁员之后,人们再也不能相信公司会全力支持他们,他们会极大地减少任何冒险的可能性。责任被嫉妒地保护着,知识被囤积,因为使自己不可替代是保护自己免受未来裁员威胁的唯一杠杆。我现在在谷歌看到所有这些。对管理层的不信任反映在管理层不再对员工显示信任,体现在愚蠢的公司政策中。2004年,谷歌的创始人曾向华尔街声称“谷歌不是一家传统公司。我们没有成为传统公司的打算。” 但那个谷歌已经不复存在。
目前,谷歌面临的许多问题主要根源于桑达尔·皮查伊缺乏前瞻性领导,并明显对保持早期谷歌文化规范的兴趣不足。这一问题的症状之一是无能的中层管理层的蔓延。
以琼恩·班克斯为例,她管理的部门包括(除其他事项外)Flutter、Dart、Go 和 Firebase。她的部门名义上有一项战略,但我无法泄露其内容;即使听了她多年的描述,我也从未真正理解其中任何部分的含义。
她对她的团队正在做的事情的理解最多也是有限的;她经常提出完全不连贯且不切实际的要求。她将工程师视为商品,以一种贬低人性的方式,以与其技能无关的方式强制重新分配人员。她甚至无法接受建设性的反馈,对此毫无回应。
据我听说,其他团队(他们的领导比我更懂政治)已经学会了如何“处理”她,以使她远离他们,恰到好处地在适当的时间提供给她所需的信息。作为亲眼见证谷歌巅峰时期的人,我对这个新的现实感到沮丧。
近年来,我开始向谷歌的任何人提供职业建议,并通过这个过程结识了公司各个地方的许多出色的人才。拯救谷歌绝非为时已晚。这需要在公司高层进行一些重大变革,将权力中心从首席财务官的办公室重新移交给具有清晰长期愿景的领导者,以有效利用谷歌广泛的资源为用户提供价值。
我依然坚信,从谷歌的使命陈述(整理世界信息,使其无所不在且有用)中仍然可以发挥巨大作用。那些愿意引领谷歌走向未来的二十年,最大化造福人类,无视股价的短期波动的人,可以将谷歌的技能和激情投入真正伟大的成就中。
然而,我认为时间正在流逝。谷歌文化的恶化最终将变得不可逆转,因为那些具备充当道德指南的能力的人正是那些不会加入没有道德指南的组织的人。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